
- 作家陶靖 LV.工兵
- 2024/4/20 7:25:06
看看这篇高考回忆录:
《高考四十年记》(转帖)
作者:万物生长
如果那年,我们多对或者多错两道题,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地方,认识完全不同的人,做着完全不同的事,错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?高考的迷人之处,不是如愿以偿,而是阴差阳错。”
又是一年高考的季节,是学生、家长外焦里嫩的季节,高考是12年寒窗苦读的结果表达方式,是人生重要的经历和资本,没有高考的人生是不丰满的。
1982年的高考,那是我的高考,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。
四十年,说短不短,说长不长。RED走出肖申克用了四十年,南唐从“凤阁龙楼连霄汉”到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不过四十年。四十年,可以让一个婴儿步入不惑,可以让一个“不惑”大概率挂掉。四十年,还可以让一个国家从羸弱不堪到厉害无比。对绝大多数人而言,四十年,就是人生的折返点,然后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。
四十年前,我们都很年轻,像刚从树上下来的猴子,清澈透明,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
四十年前的成都,主城区只有东城区、西城区,属县只有双流和金堂,周遭一众的温江、郫县、灌县、新都、崇庆、新津、彭县、大邑、邛崃、蒲江都还属于温江地区。那时成都还没有干道,也没有二环,一环也只是窄窄的二车道。那时家里还是12吋黑白电视,按键开关,拉杆天线。世界杯、女排、加里森敢死队,都拜它所赐。八一年还用它看过世界冰球C组比赛,那年中国男冰晋级B组。那时的电视尺寸和效果,别说冰球,就是冰壶也看不清楚。
四十年前,老南门旁边还有大片的农田,南门大桥附近经常有人撒网捕鱼,夏天有很多人在桥洞下游泳。
四十年前,成都还没有火锅,电话还是四位,兔脑壳五分钱一个,《电视报》五分钱一张。
四十年前,春熙路叫反帝路,石室叫四中,树德叫九中,列五叫五中。
……
我们是1980年秋进入高中的,史称“高中一九八二级”,但似乎更应该叫“高中一九八〇级”或者“高中一九八二届”。查《石室校志》,第一次称“高中××××级”是1953进校1956年毕业这届,这一届被称为“高中一九五六级”,错误从此开始,当然这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。这个错误无法纠正,只能将错就错,不然就重号了。
高中班上五十多人,来自五湖四海,猩猩29中,臭脚10中,范贼8中,阿尔卑铁中,雅各宾百花中学,田队长24中,仇万德5中,秋ber、何矮6中,政委、大忽悠14中,韩骚、夫子南桥中学,饿叶253子弟校,monkey国光子弟校,我和泡桐树、家葵以及一名女生来自四中本校。
那时成都的中学江湖,479外是川附、12中、20中、西北、5中、盐市口、13中。没有成外、实外,更没有嘉祥。那时的9中还比较弱,川附倒是有些厉害,在我们之前川附拿过一次成都高考头名。成都中学中比较意外的是成都2中,其前身是省立成都中学,名门之后,流沙河的母校,20世纪40年代与石室中学、成都县中(七中)、树德中学齐名,2、4、7也正好构成了省、府、县三级中学的完整序列。后来不知因为什么,逐渐衰落,到80年代初已经很不入流了。成都中学体育方面厉害的是7中的篮球、西北的排球、四中的篮球排球、13中的足球,田径厉害的是15中、20中。
现在石室中学门口的“文翁石室”匾额,是清嘉庆时的四川总督蒋攸铦题写,但我初中、高中时它一直挂在里面图书馆门口,我们的毕业照就是在图书馆门口照的,当时“文翁石室”就在那里。图书馆前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,一棵是银杏,另一棵也是银杏。这样牛掰的银杏成都还有两处,一是成都画院,一是028。那时大门口这个位置挂的是郭沫若的“求实务虚”,两边是郭老的对联,爱祖国爱人民、求真理求技艺什么的,白底黑字的“成都市第四中学校”则怯生生地挂在旁边的柱子上。以前四中郭老的痕迹很多,我们初中的教室就是郭老当年坐过的。“求实务虚”切换回“文翁石室”大概是在我们毕业后四中恢复“石室中学”校名时,后来,“爱祖国、求真理”也取了下来。再后来,他们把郭老和我的教室也拆了。十批不是好文章,但郭老的字是好字。
相比其他中学,石室中学有两大杀器,一个是2160多年的校史,这个不仅在全市,就是全省、全国甚至全世界,敢挑战的也不多;另一个是它有司马相如、扬雄、谯周、陈寿、李密、陈子昂、杨升庵、李调元这些校友。有了两千年的加持,有了司马相如们的站台,石室中学就躺平了,面如平湖地看着那些还在比升学率、比清华北大、比博士院士、比李易峰李稻葵的学校,有没有郭老这个校友,也就无所谓了。
四中高八二级共七个班,我们是七班,班主任刘宏吉,教英语。这七个班中一、二班是慢班,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是快班,五班在高二时成了文科班。
一、二班全是我的初中同学,我们这个初中班级是从汪家拐小学整抬进四中的,只有两个班,每班却有将近八十号人,这两个班成了四中的“初一九八零级”。初中两个班大概只有十五人考上了重点高中,有约三十人没有考上高中,剩余的百多人四中自己消化,成了高中的两个慢班,这两个班没人考上大学。
高中的语文老师叫陆懋安,西北联大毕业,语文、文学功底深厚。他只教我们一个班,我们毕业后他就退休了,所以我们是他的关门弟子,在写作方面他让我受益匪浅。高二《语文报》的全国作文竞赛,四中参赛的三人全出自陆老师这个班。高中的第一周,陆老师让写命题作文,名曰《第一次走进四中》,因为初中就是四中,所以很凡尔赛地找陆老表示疑问,但这种人陆老明显见得多了,轻松就挡了回去,“你以前是初中生进出四中,现在作为高中生不是第一次吗?!”陆老曾称散文“要像茶叶末,形散而神不散!”这句话我一直记得。“我是弹花匠的女——会谈不会纺!”这是陆老师常用的歇后语。陆老师的作文给分吝啬、评语考究,80分绝对算是高分。整个高中两年最高的一个分数是给猩猩的84分,评语“笔酣墨饱“,作文名字倒不记得了,这个分数和评语支撑了作者许多年。高考猩猩语文全年级第一,并考上成都地质学院(理工大)。除了语文,猩猩其他功课乏善可陈,但体育很厉害,我们班足球队的主力,高二校运会获得跳高第三名,并且还是游泳三级运动员,这个很罕见。他现在银行工作,吊诡的是不以写作、不以运动而是以敢说英语闻名。当时班上的文青是秋ber,七班的前卫派诗人,成名作有《栀子花》和《我爱你,花圃路》(或者是《花圃路,我爱你》)。后来考上成都电讯(电子科大),再后来,经不住烟火气的诱惑,转攻烹饪,在川菜创新上一条道走到黑。菜是越来越专精,人也越来越油腻,诗,早就不写了。雅各宾的写作比较邪性,大作是一篇名《水》的作文,还有一次命题作文——《从公孙休不受鱼谈起》,他写得离题万里,却又文采飞扬,破例得到陆老的表扬。雅各宾能写也能说,还时常语出惊人,比如他说他的北京印刷学院是印刷界的黄埔军校,这些年又说自己长得像吴秀波。另外,雅各宾还创造性地把老七班和高二转到七班的划分为“原住民”和“移民”,这是一项贡献。不过即便有老师如陆老夫子,冥顽不化的学生还是有,最典型的是韩骚,他的作文一直就没有上路。有段时间我们同桌,见过他的一篇作文被给了差评:堆砌辞藻,华而不实。还有一次自命题作文,韩骚标新立异地弄了个《再论×××××××》,这把陆老师给惹火了。韩骚这个“再论”,其实是“一论”或者“论”,但他为了表现事态胶着,二挡起步。不过韩骚的数学了得,参加过全省数学竞赛,后来也学了数学专业。
说到座位,高中两年刘老师没少折腾,先是男生女生同桌,后改成男生男生、女生女生同桌,并且自愿组合,再后来又改回男女同桌。
数学老师罗世华,总是一脑门官司,标志性的口头禅是“同学们,男同学们,女同学们”。高二时曾封七班三大懒王,分别是喻眼睛、田队长、雅各宾。
物理老师方士德,精力充沛,主观很努力。在讲解离心力时,称离心力会使旋转的物体远离它的旋转中心,要是中心的质量不够大(桩子不稳),物体就会飞出去,“那多危险!”后来在大学学了普通物理,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离心力。方老师还擅长讽刺挖苦,某天毛大迟到,方老师很是不爽,“××,你又迟到了,你都还要迟到?!”毛大非常不忿,说方老师你把我转烂了,方老师来了句“人都转得烂啊?”
化学老师周明英,中规中矩,不苟言笑,她的课很是枯燥。她儿子也在七班,初中和我是同学,成绩很差。
政治老师姓蔡云波,和另一位政治老师刘世豪是成都中学政治课的大V级人物,不走寻常路,敢说,他的课有点海派清口的意思,非常受欢迎。课堂总是笑声不断,但有一个学生从来不笑,他就是蔡老师的儿子,也是我的初中同学,后来考上西政的专科,2021年初去世了。
体育老师姓晏,名字已经记不得了。高中的体育课基本都是排球,其他很少,足球绝对禁止。有时男生也偷偷拿排球当足球踢,但当我们班的喻眼镜把六班的老孙眼睛踢伤后,就再没人敢踢了。老孙后来上了南邮,毕业后我们成了同事。
高二时四个理科快班中,成绩最好的是四班,其次三班,再次六班,最差是我们七班。普遍规律是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成反比,所以我们班的体育成绩在高八二是厉害的,尤其是男生。1981年底在市体开的四中冬季运动会上,我们班总分年级第一。我参加了接力,跑第3棒,另外三人是韩骚、调皮、饿叶。那次运动会饿叶拿了很多名次,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全才,但是七班的体育委员却不是他而是泡桐树,后者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——身高1米9。老泡是我初中同学,四中子弟,家住邮电礼堂旁边孟家巷公安厅宿舍,后来考上西南交大。
七班男生几乎都有外号,从高一下学期开始,彼此间就都以外号相称了。这些外号,或形象,或文雅,或无聊,或恶毒。“泡桐树”很形象,这家伙身高近1米9,白白胖胖的,很“泡shao”。“夫子”与韩骚都是川医子弟,这个文雅的外号怎么来的记不得了,他后来去了文科班,考上了川大。“何矮”的确矮,但很蹬度,擅长体操,着装标配是笔挺的绿色呢子衣裤配铮亮的接尖皮鞋。何矮第一年没考上,复读一年考上了厦门大学,前几年因抑郁症去世。“臭脚”是说他的脚法臭,一心想走小快灵线路,但一直没有成功,他复读一年后考上西南交大成都分校。“阿尔卑”怎么来的已经记不起,他和六班的老孙是铁路子弟,比较娇气,后来考上武汉医学院,五年学制,1986年我去武汉实习,受到他热情款待。“范贼”的由来也不可考,他后来考上川农,毕业后分到“果树办公室”,在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旁办公。“政委”是我们的班长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后来考上了南大。“调皮”是驷马桥川拖子弟,考上华东工程学院,毕业后分到35信箱。2004年还为他闹了个乌龙,那年清明去磨盘山扫墓,路过一处墓地,墓碑上墓主人的名字、年龄都与调皮相同,于是在同学中广播调皮挂了。两年后在35信箱的“光明宾馆”开会,竟然幸会了调皮本尊,流言不攻自破。“仇万德”孔武有力,当年就以江湖儿女自居。他没有参加高考,高二时选上了飞行员,因为他要入伍的缘故,我们这个班的毕业照提前了。后来转业,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,不曾想这两年突然火了,已经摇身一变,成了仇道长,道名仇至贤,头衔有中国风水大师、命理师、香港中国风水研究院院长、仇甫全盲派传人。
班上“毛大”有两位,这很不严谨。我的朋友薛总在西北上高中时,班上有两位“王保长”,人家就知道区分为“大王保长”“小王保长”,避免了混乱。所以在取外号上,四中还是不如西北。两位毛大之一是我初中同班同学,高冷,看谁都不顺眼。他高一在五班,高二转到七班,后来考上重庆交通学院,交院我常去,那里的单锅小炒是一种诱惑。另一位毛大家住老南门黉门街,当过英语科代表,没考上大学,后来做生意,再后来吸毒,这些年就没听人说起了。
饿叶、monkey都是东郊大厂子弟,东郊信箱、厂名和代号的对应关系就是他俩给我们科普的。这两人很可惜。monkey(还有个绰号叫儿子)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,但大二时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。饿叶曾在少体校练过足球,有专业水平,2003年曝光的日本人珠海招妓事件,他是涉事酒店的总经理,后被判无期。七班最让人唏嘘的是田队长,喜欢政治、哲学,高一有一阵痴迷《资本论》,差点休学,后来考上后工,三年级时服安眠药自杀。
女生有外号的不多,只记得有一个叫“DP”,有一个“臭鸡蛋”,还有一个很长,叫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。
男生没外号的不多,大忽悠是其中一个。“大忽悠”这个外号是这些年才有的,当时没有。因为浓眉大眼成绩又好,所以他可以没外号,这说明什么时候成绩好都是硬道理。尽管成绩一流,但其人举止粗鲁、崇尚暴力,曾于放学路上暴扁三班一同学,又曾带猪蹄子进清真饭馆差点被伙计暴扁。高二他是班上的文娱委员,这几十年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,这小子什么也不会。高二上学期他脸部三角区长了个大大的火疖子,本主不觉得有啥,但猩猩却认为有碍瞻观,纠集几个小兄弟,于课间设伏,将大忽悠擒获并且按倒在地,猩猩亲手把这个火疖子给挤了。因为没有采取消毒措施,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文娱委员肿着半边脸进的教室。从此后大忽悠沉默寡言专心学习,再后来他考上了北大。庆幸的是他去北大晚了63年,否则在赵家楼放火的肯定有他。
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是住校的,像我这样不住校的每天往返三次,午饭、晚饭回家吃,晚上下了自习才回家。那时我家住南郊路028,通勤方式有三种,一是坐1路公交,南郊路上南大街下(那时这一条线还叫解放南路);二是骑车走老南门大桥;三是步行走倒桑树、502厂吊桥、南城塘坎街。那时没有南门彩虹桥,也没有通祠路、文翁路,老南门大桥和百花大桥之间只有502厂吊桥,这个吊桥像都江堰的安澜索桥,摇摇晃晃,可过人过自行车。这个桥后来拆了,几乎在原位置建了一座单拱桥。这三种方式都有些绕路,比较而言走吊桥时间更可控一些。走倒桑树的话出大院马上就得左转,过杀牛巷、珠宝巷到塑料四厂路口再左转才能到倒桑树街。杀牛巷的屠宰厂那时生意还很红火,每天都有大量的水牛送进去屠宰,臭气熏天,尤其是夏天。后来修通祠路,这两条巷子就都没有了。同时期消失的还有河对岸的柳荫街,那是一条很有故事的老街,可惜了。初中就是同学的古董家住倒桑树街502厂宿舍,上学、放学我俩经常一起。古董是他初中的外号,家里叫他莽子。古董高考超水平发挥,到学校拿分数那天,他拿到成绩单后抛下同学以及他老爸,独自狂叫着一路奔跑回家,这情景让我意识到《范进中举》还是很有生活的。
那时的文庙前街,从与南城塘坎街的丁字路口到与南大街的丁字路口,是一条完整的街,后来才被文翁路截成两段。那时文庙前街有两条小巷子可通文庙后街,一条叫石室巷,一条叫孟家巷,其中石室巷也是去四中家属宿舍的通道,石室巷现在已经没有了,孟家巷好像还在。四中的对面有个红军院,据说住有老红军。出校门左拐几十米就是“邮电礼堂”(现在省电信公司的位置),那是一个对外售票的电影院,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高考前一个月,我们十多个男生晚自习时间去看了《少林寺》,刘老师为此很冒火,但因为涉及人太多,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九十年代初邮电礼堂还在,后来就消失了。文庙前街和南大街路口往老南门大桥方向有家羊肉汤,那是秋ber的最爱,经常趁着夜色去吃独食。据说两毛钱一饭盒,味道极鲜,就是饭盒不好洗。羊肉汤再往前走一点,有家“曙光”照相馆,我们毕业的单人照就是在那里照的,那天照完单人照还照了张合影,有十一位同学。沿南大街往红照壁方向,有家有名的包子——南大包,包子很大,很解馋,现在早已消失了。同样消失了的是再前面的“利宾筵”,成都餐饮老字号,工作后曾去吃过,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菜品,而是一个人称古大爷的堂倌,很老派,像郭德纲的相声那样给你介绍菜名,抑扬顿挫,点完菜后他把你的菜唱一遍,也就通知后厨了。
高中期间国内外有这么几件大事:世界杯、女排夺冠、成都大水、马岛战争。
1981年,中国男足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,平开、高走、暴跌,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让人扼腕的一次。决赛周的比赛和我们高考严重重叠,记得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。这届世界杯,尤其是中国队参加的预选赛,极大的激发了男生对足球的兴趣。高二开始,我们就时不时地去外面找场地踢足球,后来发展到班级之间比赛。和我们过招最多的是四班,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大学一、二年级,每次寒假、暑假都要比赛一场。
1981年,暑假成都连降暴雨,河水暴涨,淹了不少地方。安顺桥就是那年冲毁的,东湖就是那年形成的。大雨期间曾去古董家看望,他家住一楼,且紧邻南河。到了一看,好家伙,家里的桌椅板凳、盆盆罐罐全都漂在水中,古董拼命地往外舀水。尽管一个人在战斗,但古董全无惧色,抖擞精神,干得正欢。当时我想,这家伙不当海军真是可惜了。从502厂宿舍出来时还朝南河看了一眼,我的天,一片汪洋,根本分不清哪是河,哪是堤岸,哪是公路。古董后来考上重大,二年级时高等数学补考不及格,他认为老师刁难,于是拿了把藏式匕首去威胁老师。他给了数学老师两个选择,一是及格,一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。但剧情的发展完全没有按照古董的剧本走,既没有及格,也没有白刀子红刀子,倒是学校给了他一个取消毕业补考的处分。那时的课分考试课和考查课,考试课补考不及格在毕业时还有一次补考机会,及格后才给学位,另外如果一学期两门考试课补考不及格直接降级。后来,古董把涉案凶器送给了我。等古董再次回到学校补考及格并且拿回学位,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。
1982年的马岛战争发生时我们了解得很少,国内报道也不多。当时只记得一些关键词:加尔铁里、特混舰队、谢菲尔德号、超级军旗、飞鱼导弹等。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是年底在大学看了有关的纪录片后,印象深刻的不是战斗场面,而是英国民众为特混舰队送行的场面。大概是在朴茨茅斯,傍晚,小雨,舰艇一艘接一艘出港,水兵甲板列队,岸上一名络腮胡大汉挥舞着一面米字旗,送行的民众齐声高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
我们那一届七中高中改成三年,我们之后全部都改三年,我们是最后一届高中两年的。
当时的高考有预考,要通过预考才能参加高考,1982年的预考在5月底,科目、权重、顺序都和高考一样。数学120分,语文、物理、化学100分,英语卷面100分但七折计入总分,生物(包括生理卫生)50分,满分540分。那年预考的难度比高考大,七班上400分的只有七位。
那时的高考在7月份,四中理科在后子门的24中考,考前一天刘老师带我们看考场,从四中步行到后子门,走到一个小巷子,前面有家人在打丧火,刘老师脸色大变,令我们退回改走别的路,并且提醒每个人:明天不得经由此处!
正式的高考在7月7、8、9三天,这三天比较凉快。7日早晨6点半起床,老妈炖了锅鸡汤。七点一刻出门,规定提前一刻进考场,但四中要求提到半小时到。在24中门口遇见刘老师,问我慌不慌?我说“不慌!”我的同学们也都很镇静的样子,个个谈笑风生地,似乎胜利在握。有三个学校在24中考,除我们外是16中和24中。在等着进校门时,不少外校学生还抱着书本在看。进入考场,坐定后我环顾了一下,大多是我们班的同学。我坐最右边一列,我的左边是何矮,前面是毛大,后面是臭脚,左前是猩猩,左后是大忽悠。发完卷子没到时间不让打开卷子,这时猩猩转过头来对我说:“哥,我有点慌!”我测了下脉搏,半分钟54。
7日上午是语文,我觉得不算难。作文题目是《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》,这个题目好写。作文我写了800多字,全部做完后还剩十多分钟。下午是化学,我早早就做完了,觉得时间很富裕,反复检查了几遍。当铃响时,我收拾试卷才发现漏了一道8分的大题,这道题是最后一道,在一张半页的纸上,我居然没看见。不过分数出来后,化学却是我数理化唯一及格的一门。
8日下了一天雨,24中校园里一片泥泞。这天考三门,上午数学,下午政治、生物,数学、生物难,政治相对简单。1982年四川高考有个奇葩规定——理科数学不及格、文科语文不及格降10分投档,所以对于我们,数学不及格亏吃大了。考生物时又出了状况,我以为时间还是两个小时,实际是一小时,尽管不伤大雅,但总归是前松后紧。
9日上午是物理,下午是外语。物理有个规定很无厘头——选择题选错了倒扣分,也就是说一道小题你有得分(选对)、不得分(不选)、负分(选错)三种可能,结果没有十足把握的只有不选。考外语时我们那个教室有位外校的女生睡着了,被监考老师拍醒,但后来又睡过去了。
最后一门结束后,猩猩和我在24中门口忽悠同学出去狂欢,我俩声嘶力竭地吆喝了半天,一个响应的都没有。那些亲们,就如同刚刚经历了奥斯维辛,呆呆地看着我俩表演,不说yes也不说no,搞得我俩很是无趣。最后我和猩猩去川宾看了场电影——菲律宾的《女奴》。
那时是先填自愿后拿成绩,不像现在拿到分数再填自愿。1982年四川填报高考志愿大约在7月25日左右,而分数是7月30日才通知的。拿成绩那天我和猩猩、臭脚一起去的,到学校后才知道必须得有家长一起,大概是怕出事,于是我们分别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家长。
拿到分数等录取这段时间,是转转饭的季节,我们像一群蝗虫从这家吃到那家。那时各家的房子都不大,这十来号人,到哪家都是济济一堂的效果。
8月上旬的一天,全班去百花潭活动,这是七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,那天以后,高八二七班就解散了。这天我们班第一个录取通知——田队长的后工——到了。8月中旬,我们七八个男生又去百工堰玩了一天。
8月底,一大帮人去火车站送第一个报到的田队长,从那开始不断有同学去学校报到,后走的和在成都上学的就不断去火车送行,到后来,我也被送走了。
1982年,我们七班考上了30人左右,本科升学率接近60%,那年四川的录取率,大概在6—7%。高考后同学之间有个很大的变化——考上和没考上的两个群体,交集越来越少,来往越来越少。那些没考上的同学,好多就再没见过了。
本文开始引用的那段话,还有很琼瑶很阿Q的结尾,一并粘贴于此,以示有头有尾:
“虽然那年我错过了那道高考题,但是我却遇见了你,你是我的通知书里看不到的惊喜。如果有一天,我像哆啦A梦一样乘坐时光机,如果我又看到了高考的自己,我一定会对他说,千万不要做对那道题,因为,我还想遇见你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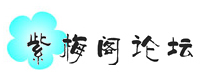 登录
注册
登录
注册
